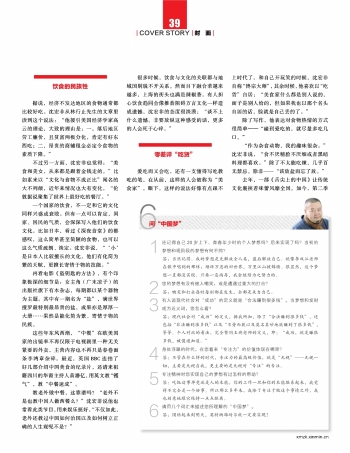据说,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食物通常都比较好吃。沈宏非从林行止先生的文章里读到这个说法:“他援引美国经济学家高云的理论,大致的理由是:一,落后地区劳工廉价,且贫富两极分化,肯定有好东西吃;二,昂贵的商铺租金必定令食物的素质下降。”
不过另一方面,沈宏非也觉得:“美食和美女,从来都是跟着金钱走的。”比如素来以“文化与食物不成正比”闻名的大不列颠,近年来情况也大有变化,“伦敦据说聚集了世界上最好吃的餐厅。”
一个国家的饮食,不一定和它的文化同样兴盛或衰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国家、国民的气质,会深深写入他们的饮食文化。比如日本,看过《深夜食堂》的都感叹,这么简单甚至简陋的食物,也可以这么气质疏朗、淡定。沈宏非说,“‘小’是日本人比较擅长的文化,他们有化简为繁的天赋,更擅长寄情于物的技能。”
再看电影《盗钥匙的方法》,有个印象极深的细节是:女主角(广末凉子)的出版社旗下有本杂志,每期都以某个器物为主题。其中有一期名为“盐”,满世界搜罗最特别最昂贵的盐,成果亦是厚厚一大册……果然是能化简为繁、寄情于物的民族。
这些年东风西渐,“中餐”在欧美国家的出镜率不再仅限于电视剧里一种无关紧要的外卖,主营内容也不再只是春卷面条李鸿章杂碎。最近,英国BBC连拍了好几部介绍中国美食的纪录片,还请来祖籍四川的华裔主持人黄瀞亿,用英文教“镬气”,教“中餐速成”。
教老外做中餐,这靠谱吗?“老外不是也教中国人做西餐么?”沈宏非说他也常看此类节目,用来娱乐挺好,“不仅如此,老外还教过中国如何治国以及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呢不是?”
很多时候,饮食与文化的关联都与地域国别脱不开关系。然而目下融合菜越来越多,上海的街头也满是辣椒香。有人担心饮食趋同会像推普阻碍方言文化一样造成遗憾,沈宏非的态度很淡漠:“谈不上什么遗憾。非要放纵这种感受的话,更多的人会死于心碎。”
零差评“吃货”
爱吃而又会吃,还有一支懂得写吃教吃的笔,在从前,这样的人会被称为“美食家”。眼下,这样的说法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。和自己开玩笑的时候,沈宏非自称“馋宗大师”,其余时候,他喜欢以“吃货”自居:“美食家什么都是别人说的,面子是别人给的,但如果我也以那个名头自居的话,脸就是自己丢的了。”
除了写作,他表达对食物热情的方式很简单——“碰到爱吃的,就尽量多吃几口。”
“作为杂食动物,我的趣味很杂。”沈宏非说,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或者黑暗料理都喜欢。”除了不太能吃辣,几乎百无禁忌。除非——“该放盐而忘了放。”
去年,一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让传统文化裹挟着味蕾风靡全国。如今,第二季